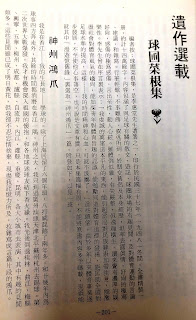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請教二事
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,請教他兩件事。一是李惠堂被傳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說。二是李惠堂的童年史。見面前幾天,我已將〈李惠堂到底有沒有被選為世界五大球王?〉https://www.inmediahk.net/node/1066381
及〈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〉http://lindapun.blogspot.com/2019/05/blog-post.html
這兩篇文章,用whatsapp傳給他看。
李炳德表示,收到這兩篇文章後,從手機轉發到家族成員的群組,現時在香港和海外的子侄有20多人,至今未收到較知情的回應。大家對這兩件事都不太清楚。
先談世界五大球王之說。他稱沒有見過相關的雜誌,父親生前也沒有向他提過此事。他個人估計,李惠堂在1976年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,是不大可能。因為既然是選舉,必然並非一個人決定,而是有較多人參與。但那時資訊、影像等傳送不及現時發達,而且李惠堂早在1947年已經掛靴,不可能在七十年代,會有很多人看過或清楚李惠堂在球場上的表現而投他的票。
另外,他認為父親是不太重視財富,卻十分重視聲譽的人。如有表揚或讚賞他的消息,他會欣然受落,不會刻意去查證或理會消息來源。所以別人有否誤傳,可能連李惠堂本人也不清楚。
他依稀記得以前有侄子提過,想尋找那本德國雜誌,但其後應該沒找到,便不見再提起。
現時發現最早刊登李惠堂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的報導,見於1976 年 6 月 4 日的《香港時報》體育版,撰文者署名原子塵。消息來源是李惠堂把那個"據悉"的報導, 私下告知原子塵。翌日,即1976 年 6 月5 日的台灣《聯合報》,改寫轉載原子塵這篇文章,刪除了原文的消息來源, 並隠掉李惠堂提及的那本西德雜誌名稱,僅稱「今年四月五日 出版的西德足球雜誌第十五期, 選出了五位全世界最有名氣的球王......」。
但現時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和台灣智慧新聞網的舊報搜索系統查找,這期間的幾份香港主要報章,包括《華僑日報》《工商日報》《大公報》,以及台灣其他主要報章,包括《中央日報》《中國時報》,都沒有關於五大球王的報導。到1979年7月4日李惠堂去世,香港的《華僑日報》《工商日報》《香港時報》《大公報》和英文《南華早報》,以及台灣《中央日報》有關他生平的報導,也沒有提及他曾當選世界五大球王。
至於李惠堂的童年史,李炳德只知父親小時候到過家鄉廣東五華,但住了多長時間?就不知道。聽過他提及小時在香港大坑,和家鄉五華,都曾以足球射牆來練習,但沒有提過射狗洞和把柚子當足球練習這些事。他認為若說到李惠堂對足球運動產生興趣,及培訓球技,那必然是在香港,不會是由五華孕育出來。民國初期香港的足球運動已蓬勃發展,與鄰近地區比較處於高水平, 那是眾所周知的事。對於大陸方面有關李惠堂童年的種種說法,他不予置評。
香港在1941年12月被日軍侵佔後,李惠堂和家人先後逃離香港,到了家鄉五華避難。李炳德是於1943年在五華出生。在家中排行最小,有三位兄長及兩位姐姐。前幾年, 三位兄長和一位姐姐已先後去世。李惠堂在1943年獨自離鄉,到了當時的陪都重慶,為國民政府服務,直至抗戰勝利才返回香港。和平後, 李炳德和留在家鄉避難的親人都回到香港生活,與李惠堂團聚。
自此,李炳德就沒有再踏足五華。父親也甚少跟他談及家鄉的事。據他所知,仍在世及常往來的家族成員也沒有和五華方面有聯繫。至今只有幾個侄約兩年前曾一起到訪過五華。李惠堂的兄弟姐妹多達六十多人,族衍龐大,網絡上有些表示與李惠堂有親戚關係的人,李炳德並不認識。
李炳德稱,過往父親的遺物全由兄長及母親保管。自八十年代後期,大陸多次有人來採訪李惠堂的生平事蹟,有說拍電影或電視劇,有說要出書,「借用」了不少李惠堂的遺物和資料,那時都由母親和兄長們出面接待這些訪客。後來李炳德才得悉,這些訪客一個都沒有回頭,取走的東西自是不知所終。所以最近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在2022年展出李惠堂的獎項或遺物,藉以介紹港人在二戰前的體育成就,李炳德卻無能為力,找不到任何父親遺物借展。
李炳德很高興近年有不少有心人整理香港的足球歷史,可惜父親生前沒有留下回憶錄或口述史,年代久遠了,整理起來便較困難。他發現有些研究者是很認真考究史實,但有些就較關注吸引讀者目光,甚至把人和事「神化」一點也覺得無所謂。很多坊間和網絡上有關李惠堂的傳聞,他都不清楚,只能留待有心人考證了。